大渡河奔涌穿過石棉縣蟹螺藏族鄉(xiāng)的群山,一株樹圍3米、樹冠如巨傘的枇杷古樹靜立八百余年。當(dāng)?shù)厝朔Q它為“老祖宗”——它是大渡河枇杷種質(zhì)的“活化石”,更是石棉成為“世界枇杷栽培種原產(chǎn)地”的見證者。
從大灣村800多年古樹下的仰望,到5.1萬畝標(biāo)準(zhǔn)果園的綿延,一場從野果到“黃金果”的變革,正從這里悄然萌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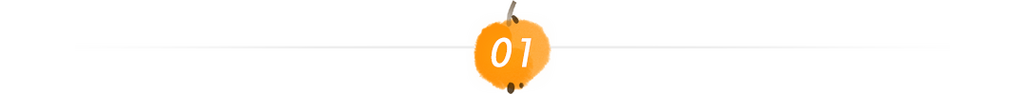
深山金果的覺醒

?1984年春,華中農(nóng)業(yè)大學(xué)的專家踩著碎石路走進石棉深山,在野生枇杷樹下駐足良久。這些酸澀的小果——本地土枇杷、大渡河枇杷、櫟葉枇杷,果實可食部分不足10%,卻讓章恢志教授眼前一亮,“能在這種環(huán)境存活,證明石棉就是種植枇杷的天選之地!”
這一發(fā)現(xiàn),揭開了石棉作為“世界枇杷栽培種原產(chǎn)地”的序幕。
四年后的1988年,春運時的一列綠皮車廂里,石棉縣農(nóng)業(yè)局科技人員康偉,一直緊盯著行李架上的100多株枇杷苗——這是從位于湖北的華中農(nóng)學(xué)院帶回的華寶2號、華寶3號、洛陽青、解放鐘等4個江浙品種。
“春運的車廂里人貼人,我不敢合眼,怕苗子被偷、怕苗子被壓壞……隔段時間,我還得給樹苗噴點水。”康偉回憶,這趟耗時6天5夜的“護苗行動”,最終讓4個新品種在今回隆鎮(zhèn)、新民鄉(xiāng)扎下根,成為石棉枇杷產(chǎn)業(yè)燎原的“第一粒火種”。
彼時的石棉人不會想到,這些擠在春運列車?yán)锏男涿纾瑢⒏膶懻麄€縣域的農(nóng)業(yè)史。

野果真能變“黃金”
起初,這些遠道而來的枇杷苗并不被看好,僅有少數(shù)農(nóng)戶敢于嘗試。在試種中,康偉從湖北帶回來的100多株枇杷苗只存活了20多株。
回隆村第一批種植枇杷苗的陳貴秀今年已經(jīng)79歲,但她仍清楚記得當(dāng)年的事情,“1.5元一株的‘金苗子’,就種在院壩邊和屋前的空地里,老羅(羅華明,陳貴秀丈夫,已去世)天天澆水,比伺候祖宗還勤快,但還是死了好多,怪可惜的。”

1991年初夏,幸存下來的枇杷樹開始掛滿金果。
“紅山了,紅山了!(方言,意為豐產(chǎn))”老羅特別興奮地喊來老伴,陳貴秀摘下一顆掰開,蜜汁順著指縫流淌,“甜得很!”
趕集日,陳貴秀背著竹簍走路到縣城,以10元一斤的“天價”售出;剩下一些賣相不好的果子,也讓陳貴秀換回了豬肉和雞蛋。
有人打趣,“這一背果子抵我小半月工資嘍!”
“一棵樹的果子賣了500元!”陳貴秀笑道,“村里人根本不信,和老羅吵嘴,氣得他一晚上覺都沒睡好。”

?從1992年開始,枇杷成了家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,供四個娃娃讀書、成家。“老羅賣了枇杷就出去旅游,走了半個中國。”陳貴秀說。
如今,陳貴秀家老屋旁,仍能看見那棵樹齡37年的“華寶2號”枇杷樹。這棵樹的枝椏上早已嫁接了“大五星”枇杷,灰褐色的樹干要比院內(nèi)的其他枇杷樹粗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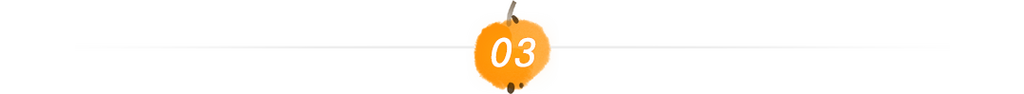
嫁接在枝頭的希望
陳貴秀家的“搖錢樹”點燃燎原之火,回隆村家家戶戶開始改種枇杷,老羅也成了科技示范戶。他家那棵“搖錢樹”收入500多元的故事,讓回隆村的枇杷樹從一棵變成一片,再變成漫山遍野。
石棉的枇杷林在繼續(xù)生長,農(nóng)技員也在繼續(xù)尋找更優(yōu)良的品種。2002年,果肉更厚、顏色更好、產(chǎn)量更高的“大五星”枇杷被引入,讓石棉的枇杷產(chǎn)業(yè)邁上新的臺階。
2010年時,豐樂鄉(xiāng)三星村的陳林也蹲在自家果園里,捏著新引進的“大五星”枝條反復(fù)比對。他虛心好學(xué),刻苦鉆研,對枇杷種植和管理有了自己的心得。

?“側(cè)枝芽苞太密,搶營養(yǎng)。”剪刀咔嚓落下,陳林獨創(chuàng)的“三層遞進修剪法”漸漸成型:初剪留4—6枝,花芽期再篩,掛果后定乾坤。
憑借著“陳氏經(jīng)驗”,他種植的枇杷個頭均勻、品質(zhì)出眾,每斤售價比市場均價高出2元。那些重達1.5兩的果實宛如小燈籠,客商爭相預(yù)付定金搶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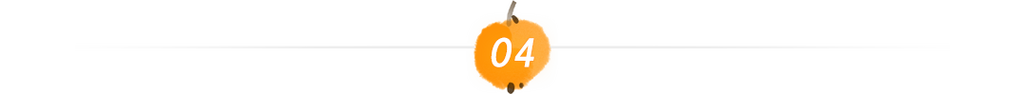
黃金時代的甜與澀
到2011年,石棉枇杷產(chǎn)業(yè)進入快速良好發(fā)展階段,“政府獎補、校縣合作、專家指導(dǎo)、農(nóng)戶跟進”的模式已具雛形,種植面積由1995年試種時的500畝擴至1.1萬畝。
從引種實驗開始,到作為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調(diào)整的重要發(fā)展樹種,石棉枇杷成為石棉縣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“十四五”期間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重要內(nèi)容,也是該縣脫貧攻堅與鄉(xiāng)村振興的重要支柱產(chǎn)業(yè)。
產(chǎn)業(yè)蓬勃發(fā)展的背后,是無數(shù)人的堅守與創(chuàng)新。

2011年,桑仕榮簽下300畝土地流轉(zhuǎn)合同那天,手有些抖——這個穿著黃膠鞋的當(dāng)?shù)毓r(nóng),把全部積蓄投入果園產(chǎn)業(yè)。
鼎盛時期,他的果園雇傭13名工人進行打理;江浙客商直接開車到地頭收購,最高收購價17元/斤。
但今年的市場讓他感到“殘酷”:枇杷集中上市,供大于求,價格跳水至3元每斤,成本難以保住。面對堆積如山的果筐,他苦笑,“走一步算一步,總有好時候。”
面對困局,唯有敢于破局,或許才能找到拐點。2025年,石棉縣與四川農(nóng)業(yè)大學(xué)共同選育的白肉枇杷“蜀白1號”通過四川省非主要農(nóng)作物品種認(rèn)定。
但是,新品種的推廣卻面臨品牌推廣培育、市場接受度等多重挑戰(zhàn)。改種面臨的風(fēng)險也讓桑仕榮“不敢輕易嘗試”。
新品種的破局仍需一場政府與農(nóng)人合力的“雙向奔赴”。這場“雙向奔赴”中,科技正成為最有力的助跑者。
當(dāng)六月的山風(fēng)掠過萬畝果園,那些金燦燦的果實里,不僅沉淀著四十余年的汗水和等待,更孕育著現(xiàn)代農(nóng)業(yè)科技的基因密碼——從智能灌溉系統(tǒng)到精準(zhǔn)農(nóng)業(yè)技術(shù),從冷鏈物流到電商平臺,石棉枇杷正在經(jīng)歷一場由科技創(chuàng)新驅(qū)動的產(chǎn)業(yè)升級。
編輯:馮方湲
責(zé)任編輯:金艷
編審:喻佳
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