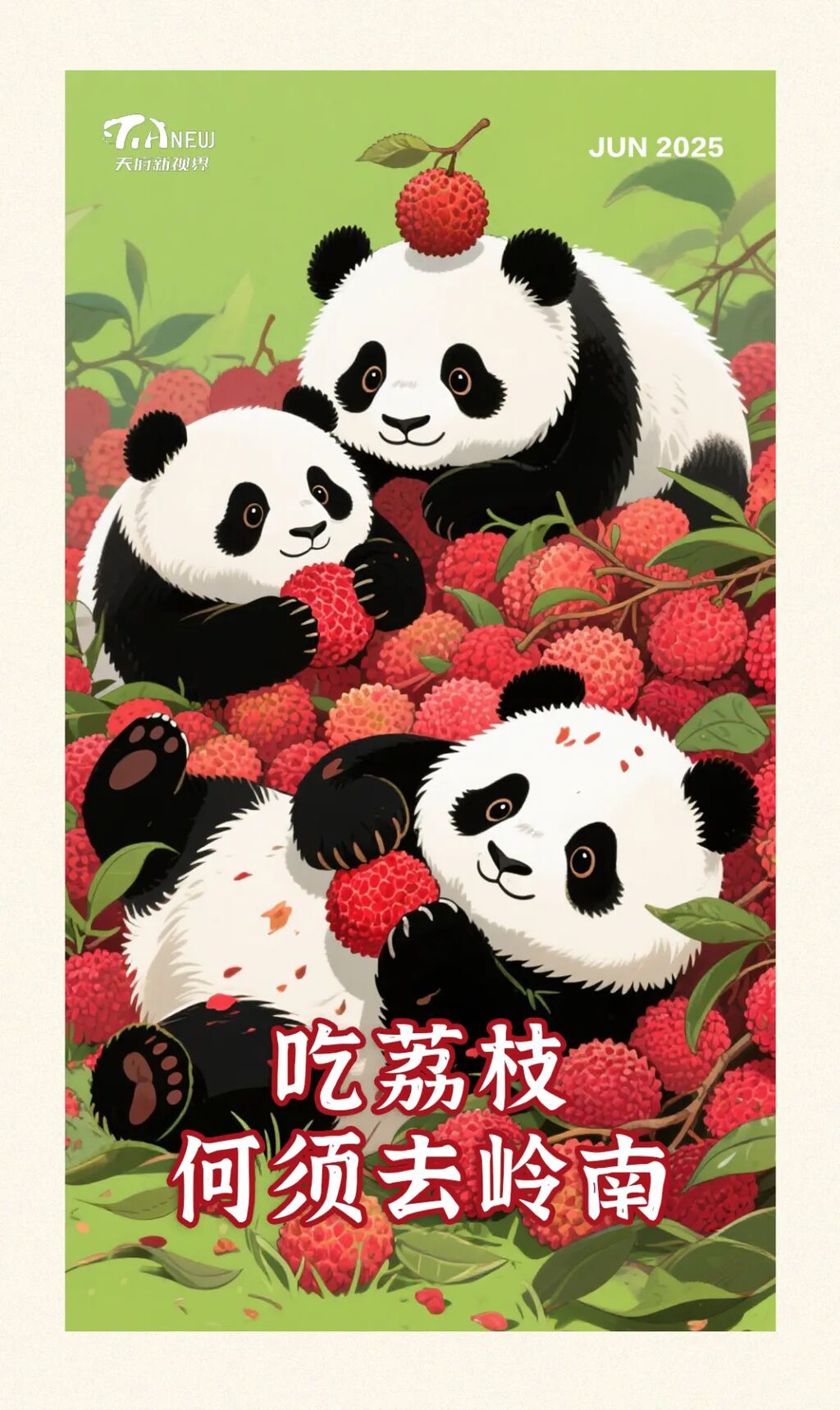
若要在水果界評選最佳“廣告文案”,杜牧與蘇軾恐怕難分高下。“一騎紅塵妃子笑,無人知是荔枝來”與“日啖荔枝三百顆,不辭長作嶺南人”,讓荔枝被“抬咖”,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水果。
不過,荔枝是種“嬌氣”的熱帶植物,氣溫低于15℃便“鬧著”要穿衣蓋被。正因如此,在熱播劇《長安的荔枝》中,李善德們才會爭分奪秒地從嶺南運荔枝到長安。
要吃荔枝,何必遠赴嶺南?四川便產(chǎn)荔枝,最古老的荔枝樹已歷經(jīng)1500余年風雨,至今仍在傳遞著盛唐的滋味。
荔枝樹喜高溫高濕,喜光向陽,5℃就是它的“生死線”,最抗寒的品種也僅能短暫抵御零下4℃的寒潮。漢武帝曾嘗試移植荔枝,甚至在上林苑修建“扶荔宮”溫室,可惜水土不服的荔枝連帝王也“扶不起”。
由此,自漢代起人們便認識到:荔枝種植的北界,止于四川。
巴蜀自古就有荔枝栽培。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載:僰道縣(今宜賓一帶)“有荔枝、薑、蒟”,江陽郡(今瀘州一帶)“有荔枝、巴菽、桃枝、蒟、給客橙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郡國志》云:“西夷有荔枝園。僰僮,施夷中最賢者。古之謂僰僮之富,多以荔枝為業(yè),園植萬株,樹收一百五十斛。”
至唐代,成都已成重要荔枝產(chǎn)地。唐代詩人張籍在《成都曲》中寫道:“錦江近西煙水綠,新雨山頭荔枝熟。”唐代女校書薛濤的《憶荔枝》更是為蜀地荔枝代言:“近有青衣連楚水,素漿還得類瓊漿”,道出了蜀中荔枝的絕佳風味。

唐代詩人白居易在《荔枝圖序》中寫道:“若離本枝,一日而色變,二日而香變,三日而味變,四五日外,色香味盡去矣。”
楊貴妃要吃新鮮荔枝,只能靠“荔枝快遞”運輸,就是杜牧詩中寫的那種場景。《唐國史補》明確記載:“故每歲飛馳以進。然方暑而熟,經(jīng)宿則敗。”科普作家史軍算過,唐代最快的馬一天跑227公里,從嶺南到長安要7天。沒有冷藏技術,要在荔枝壞掉前送到長安,幾乎不可能。
這樣看來,楊貴妃想吃新鮮荔枝,最好的選擇還是蜀地荔枝,特別是宜賓、瀘州這些傳統(tǒng)產(chǎn)區(qū)的。
《新唐書》記載,戎州(今宜賓)常把荔枝做成“荔枝煎”進貢,有鹽漬、蜜漬或糖煎等做法。杜甫在《解悶十二首》里寫過:“憶過瀘戎摘荔枝,青楓隱映石逶迤。”
四川不光有荔枝,還有運輸通道。雖然李白說蜀道難,但蜀地荔枝進長安可以走水路:先順著長江到涪陵或萬州,再走古荔枝道北上長安。這條“荔枝專線”,可能就是讓楊貴妃吃到新鮮荔枝的關鍵。

若論口福之盛,恐怕楊貴妃和唐明皇還比不上如今的尋常百姓。
如今我們品嘗到的荔枝甜美滋味,是歷經(jīng)農(nóng)人千百年選育改良的成果。即便是杜牧筆下聞名遐邇的“妃子笑”,其誕生歷史也不過百余年,不過是沾了楊貴妃和杜牧的“名人效應”罷了。
古人受限于當時的種植技術,水果品質(zhì)確實難與現(xiàn)代媲美。就連魏文帝曹丕也曾坦言,當時的荔枝滋味還不如葡萄。他在給群臣的詔書中寫道:“南方有龍眼、荔枝,寧比西國蒲萄、石蜜乎?......今以荔枝賜將吏,噞之則知其味薄矣。”這番話說得令人不禁好奇:唐代的荔枝究竟是什么味道?現(xiàn)代人還能嘗到“唐代的荔枝”嗎?
答案是肯定的。

2023年四川省公布的古樹名木名錄中,就記載著10株樹齡超過500歲的荔枝古樹。其中,宜賓市敘州區(qū)1500歲和樂山市市中區(qū)1270歲的荔枝樹,都是名副其實的“唐朝遺珍”。尤其是宜賓市敘州區(qū)定夸山山谷之中的那株“老祖宗”,說不定還是經(jīng)過“蘇軾認證”的優(yōu)質(zhì)品種。
據(jù)《四川通志》記載:“定夸山在縣西一百里。山坡荔枝連袤,多屬廖氏。”廖家與蘇軾家族有姻親關系,是蘇東坡的侄女婿,曾邀請?zhí)K軾、黃庭堅到定夸山做客。定夸山的荔枝樹主人廖致平,北宋時曾官至朝議大夫。他以蘇軾“老饕”的性子,豈有不嘗之理?

這株千年古樹至今仍“任性”地開花結果。1967年曾創(chuàng)下掛果3000余斤的紀錄,之后“休養(yǎng)”四十余年,直到2012年才再度結果。此后又沉寂多年,2023年突然碩果累累。就在人們以為它又要“休假”十年時,今年竟再度掛果。當?shù)厝苏f,這株千年古樹結出的荔枝甜中帶酸,余味悠長。
看,誰說現(xiàn)代人嘗不到唐代荔枝的滋味?
撰文/閆雯雯
編輯:余鳳
責任編輯:陳翠
編審:吳山冠

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