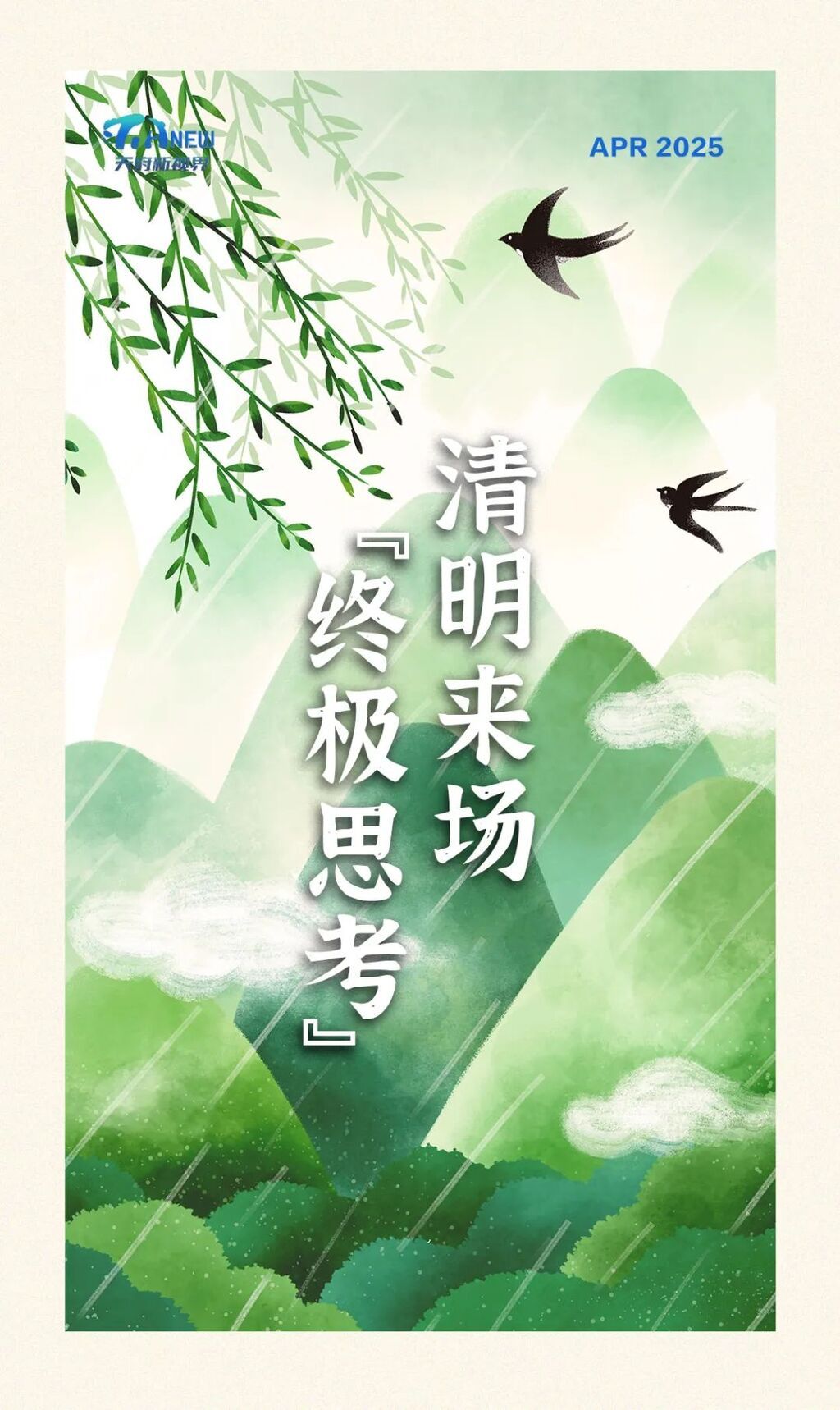
一千多年前,清明節(jié)頭號“代言人”杜牧給清明節(jié)“定調(diào)”為“雨紛紛”,再加上這又是一個(gè)寄托哀思的節(jié)日,曾引發(fā)清明節(jié)期間是否可以互祝“清明節(jié)快樂”的大討論。
清明不僅僅是“鄉(xiāng)愁”,在融匯了上巳節(jié)、寒食節(jié)等習(xí)俗后,清明也成了對于美好生活的一場“終極思考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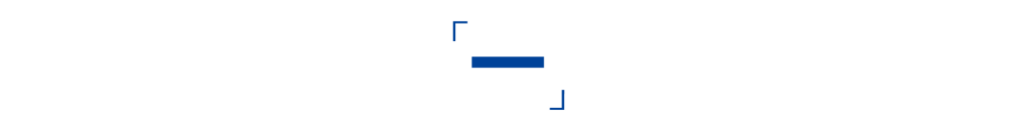
清明既是節(jié)氣,又是節(jié)日,在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價(jià)值獨(dú)顯。在二十四節(jié)氣中,它排行“老五”,能指導(dǎo)農(nóng)人“種瓜點(diǎn)豆”;又是中國四大節(jié)日之一,與傳統(tǒng)佳節(jié)春節(jié)、端午、中秋“稱兄道弟”,能享有“一天法定假期”。它不僅體現(xiàn)了源遠(yuǎn)流長的文化密碼,也是一個(gè)個(gè)家族和家庭的基因傳承,更是牽引著人們年年歸家的鄉(xiāng)愁。
制作青團(tuán)、清明馃是清明時(shí)獨(dú)特的“春日限定”,而人們更是用棉花草做出一盤可咸可甜更可口的“清明粑粑”。成都崇州元通清明春臺會,游龍舞燈,金牛鬧春,熱鬧非凡,活脫脫一幅現(xiàn)實(shí)版的“清明上河圖”。
要說川人清明活動中的“頂流”習(xí)俗,非都江堰放水節(jié)莫屬。漢代興起,北宋被確立為節(jié)日,放水節(jié)的“年齡”比清明節(jié)也沒小多少。每年冬季枯水期,人們豎榪槎、放竹籠,把內(nèi)江河水截?cái)噙M(jìn)行冬季歲修;到了來年清明,再把攔水的榪槎和竹籠拆掉,讓岷江之水沁潤川西平原的萬畝良田,用行動詮釋了何為最高級的“憫農(nóng)”。

都江堰放水節(jié)活動現(xiàn)場(資料圖) 攝影/C視覺 華小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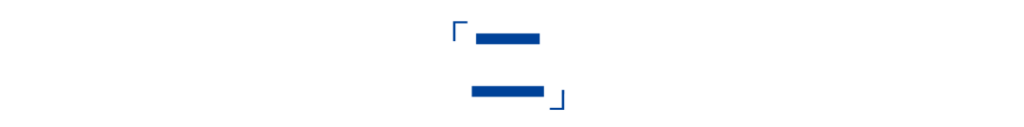
對于清明節(jié)的過法,年輕人已經(jīng)進(jìn)入了另一“次元”。
“3D建模的故鄉(xiāng)祖墳”,“AI根據(jù)老照片生成虛擬先人”讓VR掃墓成為現(xiàn)實(shí);區(qū)塊鏈祭品溯源,防止“地下房產(chǎn)證造假”。“賽博上香”的牌位和祖墳已經(jīng)被孩子們安進(jìn)了網(wǎng)絡(luò)游戲。
“創(chuàng)新”完祭掃模式,年輕人還要“創(chuàng)新”供品。香燭、紙錢、水果、鮮花都是老款式,奶茶、可樂、炸雞、漢堡主打給太公太奶們“嘗嘗鮮”。
給歷史名人掃墓,年輕人就更帶勁兒了:李白的墓前擺放著來自五湖四海的美酒,還有人送來兩罐,“一罐送李白,一罐送杜甫”;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墓前,放著“漢化大師”榮譽(yù)證書,“表彰”他在公元496年促進(jìn)了民族大融合;曹操高陵供品的特色是“醫(yī)頭風(fēng)”,據(jù)說這里布洛芬的品種應(yīng)有盡有。
當(dāng)然,年輕人能“活潑”,但該嚴(yán)肅的時(shí)候也絕不含糊。遠(yuǎn)在英國紐卡斯?fàn)柕谋毖笏畮熕沟兀迕鞴?jié)前或每逢中國海軍新航母下水,總會有人帶來最新的艦船照片;“海空衛(wèi)士”王偉烈士的墓前,每到清明節(jié)總會擺滿各種戰(zhàn)機(jī)模型,實(shí)現(xiàn)了“家祭無忘告乃翁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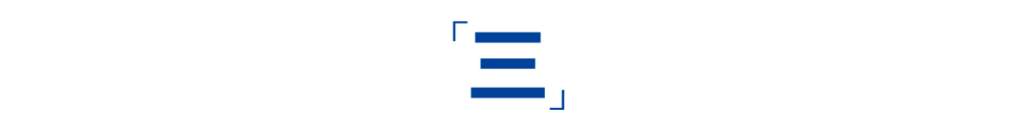
盡管清明的真諦在于“慎終追遠(yuǎn)”,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,但也不妨為這個(gè)節(jié)日戴一戴“孫悟空的金箍兒”,公序良俗始終是“緊箍咒”。
講排場、比闊氣,看誰家的昂貴祭品更多,比誰家放的鞭炮更響,仿佛只有用金錢堆砌才能彰顯對于祖先的敬意。實(shí)際上,思念的多少并不能通過祭品來衡量,寄托哀思的本質(zhì)內(nèi)涵遠(yuǎn)遠(yuǎn)大于祭掃形式本身。祭而豐不如養(yǎng)之厚,與其“沉沉夜壑燃幽炬”,不如“勸君惜取眼前人”。
文明祭掃莫“惹火上山”。春季氣溫回升,天干物燥,加上祭掃和踏青等活動增多,森林草原火災(zāi)的風(fēng)險(xiǎn)顯著增加。四川省已發(fā)布《2025年森林防火命令》和《2025年草原防火命令》,明確2025年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為1月1日至5月31日。面對本就高發(fā)的火災(zāi),對于“上墳”的民眾來說,一束鮮花,勝過冥幣紙錢,安靜告慰,好過鞭炮齊鳴。
作家史鐵生說過,“我相信,每一個(gè)活過的人,都能給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,也許是一顆巨星,也許是一把火炬,也許只是一支含淚的蠟燭。”
清明,是后人取出心中的鏡子,反射那些曾經(jīng)的光亮,告訴前人“我們沒有遺忘,我們還在前進(jìn)”的最佳時(shí)刻。
編輯:陳翠
責(zé)任編輯:余鳳
編審:吳山冠

0